中,眉 紧锁,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紧锁,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 渐消瘦的脸颊,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
渐消瘦的脸颊,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
一些新的、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用一把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切着番茄。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刀身雪白,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锋利得多。她用它切菜,几乎听不到“笃笃”的声音,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那种极其顺滑的、轻微的“嘶嘶”声。
我问她,这刀是哪儿来的。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 也不抬地说:“单位发的。说是……进
也不抬地说:“单位发的。说是……进 的,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体验一下新产品。”
的,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体验一下新产品。”
她的解释,听起来天衣无缝。
还有一次,我们家的吊扇坏了,在那个闷热的
初秋,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又提着一网兜橘子,从乡下赶了过来,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他踩着凳子,拆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灰尘,最后满 大汗地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得换个新的。
大汗地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得换个新的。
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第二天下午,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 ,抬着一台崭新的“美的”牌落地扇,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抬着一台崭新的“美的”牌落地扇,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那台电风扇,是白色的,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可以摇 ,可以定时,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
,可以定时,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
工 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统一更换老旧电器,让我们签字就行。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围着那台新电扇,啧啧称奇,一个劲儿地夸“党的政策好”,夸“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
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统一更换老旧电器,让我们签字就行。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围着那台新电扇,啧啧称奇,一个劲儿地夸“党的政策好”,夸“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
只有我知道,那天,家属院里,除了我们家,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 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她只是在签收单上,用她那手漂亮的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把那台坏掉的旧吊扇,仔仔细细地擦拭 净,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床底下。
净,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床底下。
那个晚上,舅舅赖在我们家,非要体验一下新电扇。我们三个 ,坐在桌边吃饭。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安静又柔和地吹着。舅舅吃得满嘴流油,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说这风吹在身上,感觉都比别
,坐在桌边吃饭。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安静又柔和地吹着。舅舅吃得满嘴流油,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说这风吹在身上,感觉都比别 的金贵。
的金贵。
妈妈却没什么胃 。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眼神,时不时地,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雪白的电风扇。那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朋友,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
。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眼神,时不时地,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雪白的电风扇。那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朋友,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
夜里,我被客厅里传来的、压抑的说话声吵醒。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看到舅舅和妈妈,正坐在桌边。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是舅舅的声音,他大概又喝了点酒,带着几分试探和好奇,“这又是送刀,又是送电扇的……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道?姐夫虽然没了,但咱爸这病,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妈妈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 。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程伟,不该你问的,别问。吃你的饭,住你的,再多说一句,就回乡下去。”
。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程伟,不该你问的,别问。吃你的饭,住你的,再多说一句,就回乡下去。”
“我这不是关心你嘛!”舅舅急了,“姐,你一个
 家,带着个孩子,不容易。这无缘无故的,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我怕你……我怕你被
家,带着个孩子,不容易。这无缘无故的,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我怕你……我怕你被 骗了!” 妈妈慢慢地转过
骗了!” 妈妈慢慢地转过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她说:“我自己的事,心里有数。你只要记住,安
安分分地过 子,别再给我惹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
子,别再给我惹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
舅舅被她那副样子吓住了,不敢再说话。
一个星期后,曾文静终于回到了学校。她看起来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不像以前那么有 神了。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都记在了本子上,下课后,拿给她看。
神了。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都记在了本子上,下课后,拿给她看。
“谢谢你,何晨。”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 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她一起走出校门。快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从她家那栋楼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是一个男 和一个
和一个
 的声音,
的声音,
 的声音尖利,男
的声音尖利,男 的声音压抑。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但那
的声音压抑。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但那
 躁的、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
躁的、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
我看到曾文静的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低着 ,双手紧紧地攥著书包的背带。
,双手紧紧地攥著书包的背带。
我小声问她:“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 ,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我到家了。你快回去吧。”
,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我到家了。你快回去吧。”
她说完,就匆匆地跑进了楼道,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
我站在她家楼下,还能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争吵声。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天没有来找我,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发烧。
原来,她那个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令 羡慕的家,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
羡慕的家,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
原来,她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也会藏着和我一样的、不想被 发现的秘密。
发现的秘密。
我站在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看着她家亮起灯光的窗户,心里忽然没有那么自卑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 沉的、说不清的难过。
沉的、说不清的难过。
那个秋天,我和曾文静,都长大了不少。我们都学会了,把各自家里的那扇沉重的大门,在心里,关得更紧了一些。
(5)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 冷、
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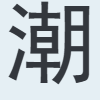 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
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 的水墨画。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的水墨画。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 笑的
笑的 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
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 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
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
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 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
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 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
 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 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
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 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 发梳得油光锃亮的
发梳得油光锃亮的 ,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
,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 体。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
体。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 ,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
,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 。我看到她漂亮的眉
。我看到她漂亮的眉 ,因为那
,因为那 浓
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