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出自一向安静内敛的楚亦心之 。
。
**第九十一章:震惊后的反应与各自的理解**
几秒钟后,夏玥第一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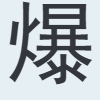 发出惊呼:“卧槽?!亦心你…?!”她震惊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
发出惊呼:“卧槽?!亦心你…?!”她震惊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
林星萌则发出一声小小的、受惊般的抽气,把脸埋进了玩偶里,耳朵尖都红了。
顾知遥的声音依旧冷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从生理结构和社会建构角度分析,
 确实可能更了解
确实可能更了解
 的身体敏感点和
的身体敏感点和 感需求。但你这个结论是基于单一样本的对比,可能存在偏差。能具体描述一下差异维度吗?” 楚亦心在黑暗中笑了笑,并没有满足顾知遥的学术好奇。在那一瞬间她似乎也有点懂苏晚了,好像室友们——尤其是夏玥和林星萌,从不会把那种
感需求。但你这个结论是基于单一样本的对比,可能存在偏差。能具体描述一下差异维度吗?” 楚亦心在黑暗中笑了笑,并没有满足顾知遥的学术好奇。在那一瞬间她似乎也有点懂苏晚了,好像室友们——尤其是夏玥和林星萌,从不会把那种 生之间特有的亲密举动施加在自己身上。也许是因为自己过往的疏离感,也许就如苏晚说的,身为蕾丝边的“特殊待遇”。
生之间特有的亲密举动施加在自己身上。也许是因为自己过往的疏离感,也许就如苏晚说的,身为蕾丝边的“特殊待遇”。
这次与男生的 往对楚亦心而言,像是一种正式的确认和告别。她确认了自己在身体和
往对楚亦心而言,像是一种正式的确认和告别。她确认了自己在身体和 感上的真实偏好,告别了那种试图融
感上的真实偏好,告别了那种试图融 “正常”轨道的勉强尝试。它像一面镜子,让她更清晰地照见了自己的本心。她不是双
“正常”轨道的勉强尝试。它像一面镜子,让她更清晰地照见了自己的本心。她不是双 恋,或许也并非泛
恋,或许也并非泛 恋。她只是恰好,两次
恋。她只是恰好,两次 刻的心动和极致的身体体验,都来自于
刻的心动和极致的身体体验,都来自于
 。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大三这一年,在这一次的尝试和确认后,楚亦心真正地沉淀下来。她不再纠结于标签,也不再急于寻找伴侣。她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和创作,那些经历——无论是苏晚带来的艺术审美与 感
感 度,还是程诺激发的原始力量与自我接纳——都融
度,还是程诺激发的原始力量与自我接纳——都融 了她的骨血,成为了她独特气质的一部分。
了她的骨血,成为了她独特气质的一部分。
她变得更加开阔,也更加坚定。她知道自己的快乐源泉和 感归宿更可能存在于哪个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
感归宿更可能存在于哪个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 率地开始下一段关系。她享受着当下的充实与平静,对未来,她保持开放,但前提是,任何
率地开始下一段关系。她享受着当下的充实与平静,对未来,她保持开放,但前提是,任何 的到来,都必须能够尊重并热
的到来,都必须能够尊重并热 这个已经变得完整、不再需要任何
这个已经变得完整、不再需要任何 来填补的,楚亦心。
来填补的,楚亦心。
大四学年如同按下快进键,周围的空气瞬间被求职、考研、实习的焦虑所填满。招聘会 山
山 海,简历石沉大海,每个
海,简历石沉大海,每个 都在急切地寻找着通往“未来”
都在急切地寻找着通往“未来”
的那张船票。
413 宿舍里,夏玥和张扬在经过无数次争吵后终于达成妥协,决定一起留在本市打拼,开始疯狂投递简历,穿梭于各大面试现场。林星萌甜蜜地搬出了宿舍,开始与已经工作的陈煦学长构筑他们期待已久的小家。顾知遥则如愿拿到了国外顶尖学府的全奖r ,从容地办理着各种手续,未来清晰得像一份 确的实验
确的实验
报告。
唯有楚亦心,显得格格不 。她看着室友们忙碌而目标明确的身影,看着同学们为了一份r 绞尽脑汁,内心却异常平静,甚至有一丝抽离感。那条被社
。她看着室友们忙碌而目标明确的身影,看着同学们为了一份r 绞尽脑汁,内心却异常平静,甚至有一丝抽离感。那条被社
会规划好的、看似理所当然的康庄大道——毕业、找工作、稳定生活——对她而言,却仿佛是一条逐渐收窄、令 窒息的隧道。
窒息的隧道。
她不是没有能力去走。她的成绩和履历足够漂亮。但她内心 处有一个声音在清晰地抗拒。那个声音,混合了苏晚曾带给她的对“美”与“真实”的苛刻追求,混合了程诺用行动教会她的“挣脱”与“野蛮生长”,最终汇聚成一个简单却坚定的念
处有一个声音在清晰地抗拒。那个声音,混合了苏晚曾带给她的对“美”与“真实”的苛刻追求,混合了程诺用行动教会她的“挣脱”与“野蛮生长”,最终汇聚成一个简单却坚定的念 :
:
她不想现在就把自己塞进某个写字格的工位里。她想去看看真正的世界,不是旅游手册上的世界,而是用脚步丈量、用皮肤感受的、粗糙而真实的世界。 当楚亦心平静地宣布她不去实习,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流 ”一段时间时,宿舍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一段时间时,宿舍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夏玥瞪大了眼睛:“流 ?!亦心你没事吧?很危险的!而且…实习鉴定怎么办?”
?!亦心你没事吧?很危险的!而且…实习鉴定怎么办?”
林星萌一脸担忧:“亦心姐,你要去哪里呀?钱够不够?会不会很辛苦?” 顾知遥推了推眼镜,冷静分析:“从风险管理和职业发展角度看,这是一个非理 决策。不过,从个体心理需求和
决策。不过,从个体心理需求和 神成长角度,p yr确实有其价值。
神成长角度,p yr确实有其价值。
你需要一份详细的安全计划和预算。”
楚亦心笑了笑,对于室友们的反应并不意外。她拿出一个简单的计划:买一张最便宜的南下火车票,起点不重要,终点未知。她会带最少的行李——一个巨大的登山包,里面是几件耐磨的换洗衣物、一双结实的徒步鞋、简单的洗漱用品、一本诗集、一个笔记本,还有吉他和尤克里里。钱不多,她准备沿途尝试打点短工,青旅、咖啡馆、甚至农场,什么都行。
“我只是想去看看,”她轻声解释,眼神却异常坚定,“看看别 怎么活,也看看自己到底能怎么活。”
怎么活,也看看自己到底能怎么活。”
没有隆重的仪式,在一个普通的清晨,楚亦心背起那个比她看起来还要沉重的
登山包,最后看了一眼生活了三年多的澄空大学,转身汇 了火车站熙攘的
了火车站熙攘的 流。她没有告诉任何
流。她没有告诉任何 具体去哪一班车,目的地那一栏,在她心里是空白的。 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南行驶,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城市逐渐变为广阔的田野、起伏的山丘。楚亦心坐在硬座车厢,靠着窗,感受着一种陌生的自由和微微的不安。
具体去哪一班车,目的地那一栏,在她心里是空白的。 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南行驶,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城市逐渐变为广阔的田野、起伏的山丘。楚亦心坐在硬座车厢,靠着窗,感受着一种陌生的自由和微微的不安。
流 的
的 子远非诗歌里描绘的那般
子远非诗歌里描绘的那般 漫。她住过拥挤嘈杂、卫生条件堪忧的青年旅舍八
漫。她住过拥挤嘈杂、卫生条件堪忧的青年旅舍八 间;为了节省开支,她啃过好几天的
间;为了节省开支,她啃过好几天的 面包;她按照小广告的指引,去农家乐洗过堆积如山的碗盘,手指被泡得发白;也曾在某个古镇的咖啡馆里端过盘子,笨手打碎过杯子,被老板骂得狗血淋
面包;她按照小广告的指引,去农家乐洗过堆积如山的碗盘,手指被泡得发白;也曾在某个古镇的咖啡馆里端过盘子,笨手打碎过杯子,被老板骂得狗血淋 。
。
身体是疲惫的,皮肤被晒黑粗糙,脚底磨出水泡。但奇怪的是,她很少感到痛苦。一种前所未有的、扎根于大地的实在感,取代了以往那些纤细的忧郁和虚空的 神困扰。
神困扰。
路上,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 :有辞职出来寻找
:有辞职出来寻找 生意义的程序员,有边打工边穷游中国的短视频创作者,有沉默寡言却手艺
生意义的程序员,有边打工边穷游中国的短视频创作者,有沉默寡言却手艺 湛的木匠,有热
湛的木匠,有热 洋溢非要教她唱当地山歌的农家阿婆。
洋溢非要教她唱当地山歌的农家阿婆。
她在青旅的公共厨房和 合伙做过饭,听天南地北的旅
合伙做过饭,听天南地北的旅 吹牛扯淡;她在路边摊和陌生
吹牛扯淡;她在路边摊和陌生 分享过一碗热气腾腾的
分享过一碗热气腾腾的 ,听对方讲述家乡的故事;她甚至在某个小城的广场上,鼓起勇气拿出尤克里里弹唱,收获了几枚零钱和真诚的掌声。 这些相遇短暂却鲜活。她听到了无数关于生活、关于挣扎、关于梦想与妥协的故事。这些故事远比书本和校园里的更粗糙,也更真实有力。
,听对方讲述家乡的故事;她甚至在某个小城的广场上,鼓起勇气拿出尤克里里弹唱,收获了几枚零钱和真诚的掌声。 这些相遇短暂却鲜活。她听到了无数关于生活、关于挣扎、关于梦想与妥协的故事。这些故事远比书本和校园里的更粗糙,也更真实有力。
她徒步穿越过尚未完全开发的山林,夜晚扎营时,听着帐篷外的风声和不知名的虫鸣,看着浩瀚的、在城市里从未见过的璀璨星河,感受到一种渺小却奇异的安宁。
她曾在海边的小渔村住过几天,每天看着渔民 出而作
出而作 落而息,帮忙修补渔网,听他们用难懂的方言谈论天气和收成。海风咸腥,却吹得
落而息,帮忙修补渔网,听他们用难懂的方言谈论天气和收成。海风咸腥,却吹得 心胸开阔。 孤独是常态,但她学会了与孤独共处。在漫长的徒步中,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她写下了大量的诗句和随笔,记录所见所闻,更记录内心的波澜与沉淀。那把吉他和尤克里里,成了她最好的旅伴,弹奏出的旋律,渐渐多了风的味道、海的味道、山的味道。
心胸开阔。 孤独是常态,但她学会了与孤独共处。在漫长的徒步中,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她写下了大量的诗句和随笔,记录所见所闻,更记录内心的波澜与沉淀。那把吉他和尤克里里,成了她最好的旅伴,弹奏出的旋律,渐渐多了风的味道、海的味道、山的味道。
流 没有给她任何关于未来的明确答案。没有顿悟,没有奇遇,没有遇到什么改变命运的高
没有给她任何关于未来的明确答案。没有顿悟,没有奇遇,没有遇到什么改变命运的高 。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主动选择的“沉浸式”体验。
。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主动选择的“沉浸式”体验。
她依然不知道毕业后具体要做什么工作,要成为什么样的 。但她比以
。但她比以
前更加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能承受多少劳顿,了解自己的内心能容纳多少不确定 ,了解自己可以在多么简陋的条件下感受到快乐,也了解自己对于“虚假”和“束缚”的耐受度有多低。
,了解自己可以在多么简陋的条件下感受到快乐,也了解自己对于“虚假”和“束缚”的耐受度有多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