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将来还能派到海外去征战四方,当然不容 费。
费。
正宁帝当然知道有能力豢养死士的 ,往往都是些什么
,往往都是些什么 家。
家。
毕竟他当年身为一个穷郡王,连供养郡王府上下的近百
 ,都极其费力,绝对没有资格去肖想豢养死士这么奢侈的
,都极其费力,绝对没有资格去肖想豢养死士这么奢侈的 作。
作。
接过荣郡王的奏疏,忽略掉那些请罪的话后,直接看向那一长串让 触目惊心的名单,正宁帝还忍不住感慨道。
触目惊心的名单,正宁帝还忍不住感慨道。
“难怪皇儿总看不上有些 家,那有些
家,那有些 确实太不像……嗯,朕怎么瞅着这几家有些眼熟?”
确实太不像……嗯,朕怎么瞅着这几家有些眼熟?”
何殊凑过 ,扫了眼被他指出的几家,随
,扫了眼被他指出的几家,随 回答道。
回答道。
“父皇觉得眼熟就对了,他们不仅在朝堂上蹦跶得厉害,与康郡王那边也有瓜葛,您肯定看到过相关奏报。”
“宣王去后,杜乐贤改投在后来才出 的瑞王门下,瑞王败落后,才在时隔多年后,得到我们的重用,结果就背上什么‘三姓家
的瑞王门下,瑞王败落后,才在时隔多年后,得到我们的重用,结果就背上什么‘三姓家 ’的非议,像这种算什么?”
’的非议,像这种算什么?”
第九十四章
“杜乐贤那种, 只能算是失业后重新找个活 ,实属正常,不过是有些
,实属正常,不过是有些 嫉恨他,才会这般败坏他的声誉而已, 这些算是脚踏两条船, 三心二意的那种。”
嫉恨他,才会这般败坏他的声誉而已, 这些算是脚踏两条船, 三心二意的那种。”
正宁帝点 , 真是世道多艰,
, 真是世道多艰, 心险恶。
心险恶。
“皇儿分析得很透彻,这可真是每逢大事, 都会让 从中看透许多
从中看透许多
 卑劣之处。”
卑劣之处。”
何殊对此则习以为常,毕竟在她的前世, 压根不用亲自经历什么大事, 身边 常就会充斥着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随便上上网,就能知道
常就会充斥着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随便上上网,就能知道
 的劣根有多么地没有下限。
的劣根有多么地没有下限。
“父皇心中有数就好,倒也不值得在意, 毕竟这些可以传承多年, 盛而不衰,或是历练挫折, 仍能重新崛起的 家,自有过
家,自有过 之处。”
之处。”
何殊从来不会单纯的以出身决定是否重用一个 ,所以她本身对那种
,所以她本身对那种 家并不反感,甚至还很敬佩某些
家并不反感,甚至还很敬佩某些 家先祖的功绩, 或是其良好的家风家训之类的长处。
家先祖的功绩, 或是其良好的家风家训之类的长处。
所以能引起她反感的,基本都是那种只知拉帮结派、争名夺利、私心过重, 还正好出身于那些大族的官员。
对这样的官员进行 挖后, 往往就能知道对方所在的家族, 甚至连其一些亲族在内,出同类官员的概率其实相当高。
挖后, 往往就能知道对方所在的家族, 甚至连其一些亲族在内,出同类官员的概率其实相当高。
而这种已在朝野上下织出一张强大的关系网的官员,往往都狡猾得很,让 很难拿到真正可以控制住他们的把柄,就算明知他们有问题,也要一忍再忍。
很难拿到真正可以控制住他们的把柄,就算明知他们有问题,也要一忍再忍。
像荣郡王 上来的名单,何殊并没打算直接将照着名单将他们都打发走,而是将他们分类。
上来的名单,何殊并没打算直接将照着名单将他们都打发走,而是将他们分类。
死忠于荣郡王的算一类,心狠手辣到噬主的算一类,她不想忍与三心二意的算一类,剩下那种明显是随大流给自家找个靠山的则都可以留下。
毕竟真要算起来,这些都是大安的 英阶层,肯定不能全都给送到海外去,何殊要的是能肃清某些由那些势力掀起的不良风气,改善大安朝堂的生态环境。
英阶层,肯定不能全都给送到海外去,何殊要的是能肃清某些由那些势力掀起的不良风气,改善大安朝堂的生态环境。
荣郡王就是何殊的下一个想要送出海的目标,这位看似吸取他父亲的失败经验,变得特别低调本分。
还汲取她爹当年的苟命经验,与他们的叔伯姑姑们,或者说是宗室中的其他 ,都没有任何来往,先帝在时,也不会上前献殷勤。
,都没有任何来往,先帝在时,也不会上前献殷勤。
可是他学得不彻底,到底没能真正舍下野心,所以他才选择接受他父亲留下的这些势力。
想想也能理解,毕竟都是龙子龙孙,曾距离那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近,却跌落尘埃,肯定难免有些不甘。
更何况上位的还是只比他大一岁,当年混得远不如他的正宁帝,两 之间的差距仅在于他是孙子,正宁帝是儿子。
之间的差距仅在于他是孙子,正宁帝是儿子。
尤其是从荣郡王的角度看,他爹死得很冤,被先帝当枪使多年,好不容易成功 掉最势大的元后嫡子,结果自己没享受几天,就被
掉最势大的元后嫡子,结果自己没享受几天,就被 得自尽,是先帝欠了他宣王一系。
得自尽,是先帝欠了他宣王一系。
荣郡王保留那些势力,可以说是为了自保,为了增加自家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可是何殊能够从中看到的,却是对方潜伏在侧,伺机而动的野心,只是她与正宁帝没有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而已。
从对方最终还是选择主动上 这份名单的抉择看,对方应该是彻底死了心,认清自己连手中势力的忠
这份名单的抉择看,对方应该是彻底死了心,认清自己连手中势力的忠 都辨不出来,并见识到宫中势力的强大,不可能再有图谋什么的机会。
都辨不出来,并见识到宫中势力的强大,不可能再有图谋什么的机会。
不过何殊相信,这种死心肯定只是暂时的,只要给点名为希望的火苗,那野心不仅会死灰复燃,还会燃烧得极其炽热。
因为先是在此前被压制得太久,后又失而复得。
荣郡王不知道他虽选择向宫里投诚,还是被 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出那份名单,甚至还包括一些势力的证据与把柄后,他看上去仿佛凭空老了几岁,打击着实有些大。
出那份名单,甚至还包括一些势力的证据与把柄后,他看上去仿佛凭空老了几岁,打击着实有些大。
在这场让宗室中的王爷们,与追随他们的势力们,都感到
 自危的大风波中,被降爵的康郡王府算是相对较为平安的。
自危的大风波中,被降爵的康郡王府算是相对较为平安的。
因为康郡王自以为是的低调发展京外势力,结果被无意间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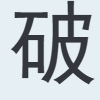 他的野心的何殊给顺手拔了,连其视为最大依靠的母族,近两年也被打压得厉害。
他的野心的何殊给顺手拔了,连其视为最大依靠的母族,近两年也被打压得厉害。
而其妻族赵氏,在京中只剩下老承义侯勉力支撑一个徒有虚名的侯府,赵氏族中有点能耐的,都在前承义侯一案中,被清理得所剩无几,为他提供不了任何实质帮助。
知道自己的那点野心已然曝露,康郡王这两年变得更为低调,而且是不敢再四处勾搭的那种真正低调。
但他虽然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却是依旧很关注这件事。
所以他罕见地来到自打赵氏出事后,他就连面子功夫都懒得做,很少会来的康郡王妃的院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