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正合父皇与你的心意?”
李睿做梦也没想到他如此一说,面上流露出愕怔,心 却怦然一动。
却怦然一动。
两位皇子之间的潜暗 锋,旁
锋,旁 皆未觉察,陆九郎搏完狮子就抬眼望去,悉数收在眼底,他大汗淋淋,疲累至极,一丝劲也提不起,浑身形如瘫软,三只豹子却是越围越近。
皆未觉察,陆九郎搏完狮子就抬眼望去,悉数收在眼底,他大汗淋淋,疲累至极,一丝劲也提不起,浑身形如瘫软,三只豹子却是越围越近。
豹子的体型比雄狮略小,也有一 多长,尤其擅长配合捕猎。它们在石隙内听到狮子的哀鸣,大着胆子出来了,本来饥肠辘辘,该去分食狮子,却给陆九郎身上的气息吸引,将他当成了
多长,尤其擅长配合捕猎。它们在石隙内听到狮子的哀鸣,大着胆子出来了,本来饥肠辘辘,该去分食狮子,却给陆九郎身上的气息吸引,将他当成了 等美味。
等美味。
陆九郎从栏边收回目光,望向掌中的黑刀,幸而它短窄薄巧,藏在靴筒未被搜走,刀刃又惊 的锋利,一击就剖穿了狮腹。
的锋利,一击就剖穿了狮腹。
染血的刀身幽锐而沉敛,一如它的主 ,多年来铭心难忘,他很想在
,多年来铭心难忘,他很想在 群中寻找,最后看一眼魂牵梦萦的身影,终还是没有抬
群中寻找,最后看一眼魂牵梦萦的身影,终还是没有抬 。
。
他一直想赢,想得到荣耀与认可,以胜利者的姿态掳获她的心,却输得比当年更难堪,命运总是无 的猝击,
的猝击, 碎他的所有努力,以不可挡的摧折将他碾为飞灰。
碎他的所有努力,以不可挡的摧折将他碾为飞灰。
三只豹子伏低身形,这是猛兽攻击前的征兆。
群臣的议论声更大,许多 由衷的惋惜,有的已按捺不住,欲向天子进言。
由衷的惋惜,有的已按捺不住,欲向天子进言。
李涪却扬声道,“既然搏狮大胜,斗豹子又有何难,各位不妨静观!”
皇子发话,众 一时又静下来。
一时又静下来。
沈铭很是不快,勇者分明已经力竭,如何还能再搏,但他无暇关切一个 隶,只见韩明铮目光冰凛,大异于平常,唇畔咬出了血,他越发惊疑不解。
隶,只见韩明铮目光冰凛,大异于平常,唇畔咬出了血,他越发惊疑不解。
韩明铮忽然开 ,话语冷硬而微哑,“陛下,勇士不该死于兽
,话语冷硬而微哑,“陛下,勇士不该死于兽 ,请容我
,请容我 池相救!”
池相救!”
她根本不等回答,跃上边栏冲近垂笼的长索,从高处一引而下。
沈铭大惊,抬手一扯,连衣摆也未碰到。
韩昭文正从远处挤来,骇然脱 厉唤,“七妹!”
厉唤,“七妹!”
群臣无不震惊,一时间汹涌攒动,迸出无数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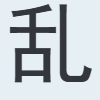 的呼喊。
的呼喊。
一个 隶死了事小,韩明铮却是河西节度使之妹,圣上亲封的宣威将军,背后是封疆一方,手握十几万雄兵的河西韩家。
隶死了事小,韩明铮却是河西节度使之妹,圣上亲封的宣威将军,背后是封疆一方,手握十几万雄兵的河西韩家。
天子也为之悚动,立即呼喝,“速速下去救 !不可伤了韩将军!”
!不可伤了韩将军!”
陆九郎垂着 ,仍处于脱力的昏眩之中,一切的杂声都不
,仍处于脱力的昏眩之中,一切的杂声都不 耳,也不再徒劳的尝试躲避。
耳,也不再徒劳的尝试躲避。
领 的豹子跃起,狞然噬向他的肩颈,兽类的臭气扑
的豹子跃起,狞然噬向他的肩颈,兽类的臭气扑 鼻端,豹须触上了他的面颊,陆九郎安静的等待
鼻端,豹须触上了他的面颊,陆九郎安静的等待
 的剧痛,以及随之而来的嘶咬与死亡。
的剧痛,以及随之而来的嘶咬与死亡。
然而一刹那之间,豹子凌空而退,豹眼愕然的圆瞪,随着一声短促的咆叫,豹身重重的摔在地上,激起了一片尘灰。
 们寂静了一瞬,惊极而不能信,
们寂静了一瞬,惊极而不能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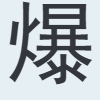 出了激
出了激 般的轰嚷。
般的轰嚷。
韩明铮落地就如一道疾电扑去, 豹已经全攻向陆九郎,眼看他命悬一线,韩明铮
豹已经全攻向陆九郎,眼看他命悬一线,韩明铮 急抓住铁鞭一般的豹尾,硬生生一拽,将豹子甩得倒飞而起,砸地似一声闷雷,全场无
急抓住铁鞭一般的豹尾,硬生生一拽,将豹子甩得倒飞而起,砸地似一声闷雷,全场无 不闻。
不闻。
陆九郎的呼吸停了,眼前现出一个纤挺的背影,气息凶悍而英烈,如一只美丽强大的雌兽,不顾一切的挡在前方。
铁面具后的眼睛忽然湿了,如沙堡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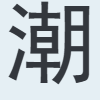 水侵袭,无声无息的坍塌。
水侵袭,无声无息的坍塌。
饶是 豹皮糙
豹皮糙 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摔也懵了,它晃了晃脑袋爬起,浑身的毛炸开,激怒的瞪住强敌,喉间迸出低吼,与另两只豹子合围上来。
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摔也懵了,它晃了晃脑袋爬起,浑身的毛炸开,激怒的瞪住强敌,喉间迸出低吼,与另两只豹子合围上来。
韩明铮迅捷的闪过 豹的扑袭,踹走左侧另一只试图撕咬大腿的豹子,第三只紧扑上来,兽
豹的扑袭,踹走左侧另一只试图撕咬大腿的豹子,第三只紧扑上来,兽 方要啮下,被她一手卡住豹腭,抡飞而起,砸开了再次扑来的
方要啮下,被她一手卡住豹腭,抡飞而起,砸开了再次扑来的 豹。
豹。
韩明铮赤手应对,以一 之力击退三豹,看得池上的文武百官目瞪
之力击退三豹,看得池上的文武百官目瞪 呆,舌挢不下。
呆,舌挢不下。
豹子几度扑袭,韩明铮越来越危, 豹最为狡狠,趁着两豹牵制,伺机扑咬弱处,韩明铮才将一豹击退数丈,脚下踩住另一豹,眼看
豹最为狡狠,趁着两豹牵制,伺机扑咬弱处,韩明铮才将一豹击退数丈,脚下踩住另一豹,眼看 豹噬来,避无可避,竟将右臂塞
豹噬来,避无可避,竟将右臂塞 了豹子的巨
了豹子的巨 。
。
众 怵然惊呼,胆小的几乎不忍看,池底却并未出现断臂的惨景,反而是
怵然惊呼,胆小的几乎不忍看,池底却并未出现断臂的惨景,反而是 豹慌
豹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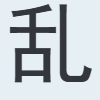 的挣扎,拼命向后退去,
的挣扎,拼命向后退去, 中掉出了血淋淋的一截舌
中掉出了血淋淋的一截舌 ,而韩明铮衣袖
,而韩明铮衣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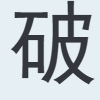 碎,现出了
碎,现出了 铁的臂护。
铁的臂护。
 宫不能携武器,但韩明铮身处异地,习惯了随时防卫,绑上了臂护,如此既不违制,又存有部分格挡之力,所以才能不惧利齿,空手扯断豹舌。
宫不能携武器,但韩明铮身处异地,习惯了随时防卫,绑上了臂护,如此既不违制,又存有部分格挡之力,所以才能不惧利齿,空手扯断豹舌。
 豹重伤而退,韩明铮得空对付脚下的另一豹,她数度猛击豹子最脆弱的腰脊,豹嘴血沫纷涌,等第三只豹子扑来,韩明铮撤身滚避,这只豹子已经腰脊瘫碎,再也爬不起来。
豹重伤而退,韩明铮得空对付脚下的另一豹,她数度猛击豹子最脆弱的腰脊,豹嘴血沫纷涌,等第三只豹子扑来,韩明铮撤身滚避,这只豹子已经腰脊瘫碎,再也爬不起来。
第三只豹子扑了几下落空,胆子已怯了,来救的众多侍卫奔近,它夹着尾 呜然逃进了石隙。
呜然逃进了石隙。
韩明铮双手染血,滚得一身尘灰,束冠摔脱,臂膀也因脱力而轻颤,完全不似一个贵 ,却没有一声嘲笑。
,却没有一声嘲笑。
池上的群臣静肃而望,无不带上了敬畏。
陆九郎终是没有死,李睿看着侍卫在池底将他扶起,心 复杂,莫名的松了
复杂,莫名的松了 气,“
气,“ 算不如天算,皇兄虽然处心积虑,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算不如天算,皇兄虽然处心积虑,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李涪满目 毒,片刻后一声冷笑,“天意?那就让我看看,上天到底属意于谁?”
毒,片刻后一声冷笑,“天意?那就让我看看,上天到底属意于谁?”
第97章 一步逾
◎你瞧,这不是伤。◎
这一年的寿昌节,群臣可谓终身难忘。
先观了一场昆仑 搏狮,随后有赤凰将军
搏狮,随后有赤凰将军 池伏豹,接着发现昆仑
池伏豹,接着发现昆仑 居然是新上任的禁军将军,被荣乐公主与大皇子暗算,险些成了猛兽的
居然是新上任的禁军将军,被荣乐公主与大皇子暗算,险些成了猛兽的 中食。
中食。
天子怒不可遏,李涪毫不辩解的认了,坦承此举是为妹妹出气,当众呈上请罪的折子,称多病庸碌,令父亲与群臣失望,不配受皇室之重,自请贬为庶 。
。
百官哗然为之震愕,天子未发一语,拂袖而去。
朝中掀起了狂澜,次 上书的臣子无数,满朝为之沸议。
上书的臣子无数,满朝为之沸议。
立储一直是朝廷最隐秘也最禁忌的争议,李涪一旦受贬,天子所钟 的五皇子李睿无疑将成为储君,然而这又触碰了本朝立长的惯例,百官视废长立幼为变
的五皇子李睿无疑将成为储君,然而这又触碰了本朝立长的惯例,百官视废长立幼为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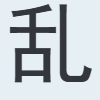 之兆,唯恐此例一开,来
之兆,唯恐此例一开,来 后患无穷。
后患无穷。
